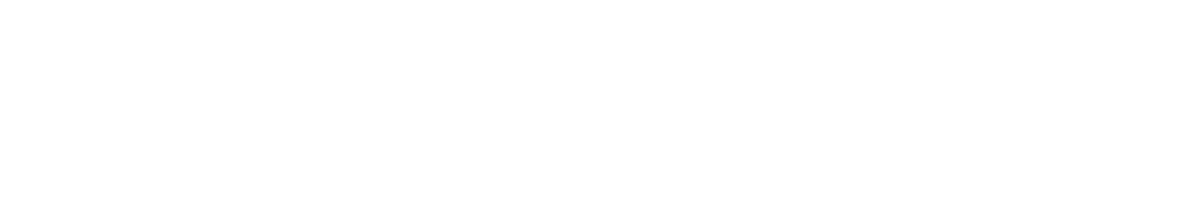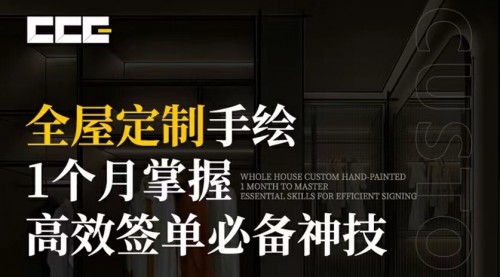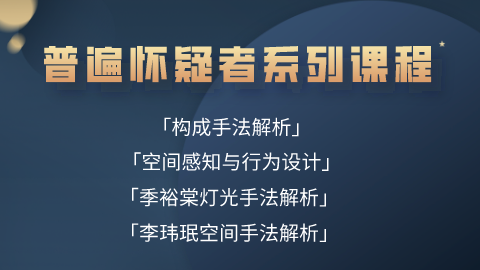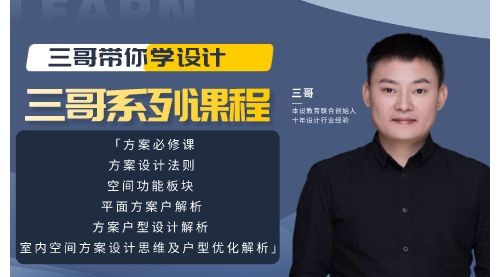| |
序赞编辑 未来城市,室内设计-3979294728331
灵感案例
交流论坛
设计资源
关注我们
VssZan.com © Copyright By 佛山市视序澎湃科技有限公司

 发表于 2024-10-17 14:04:13
发表于 2024-10-17 14:04:13